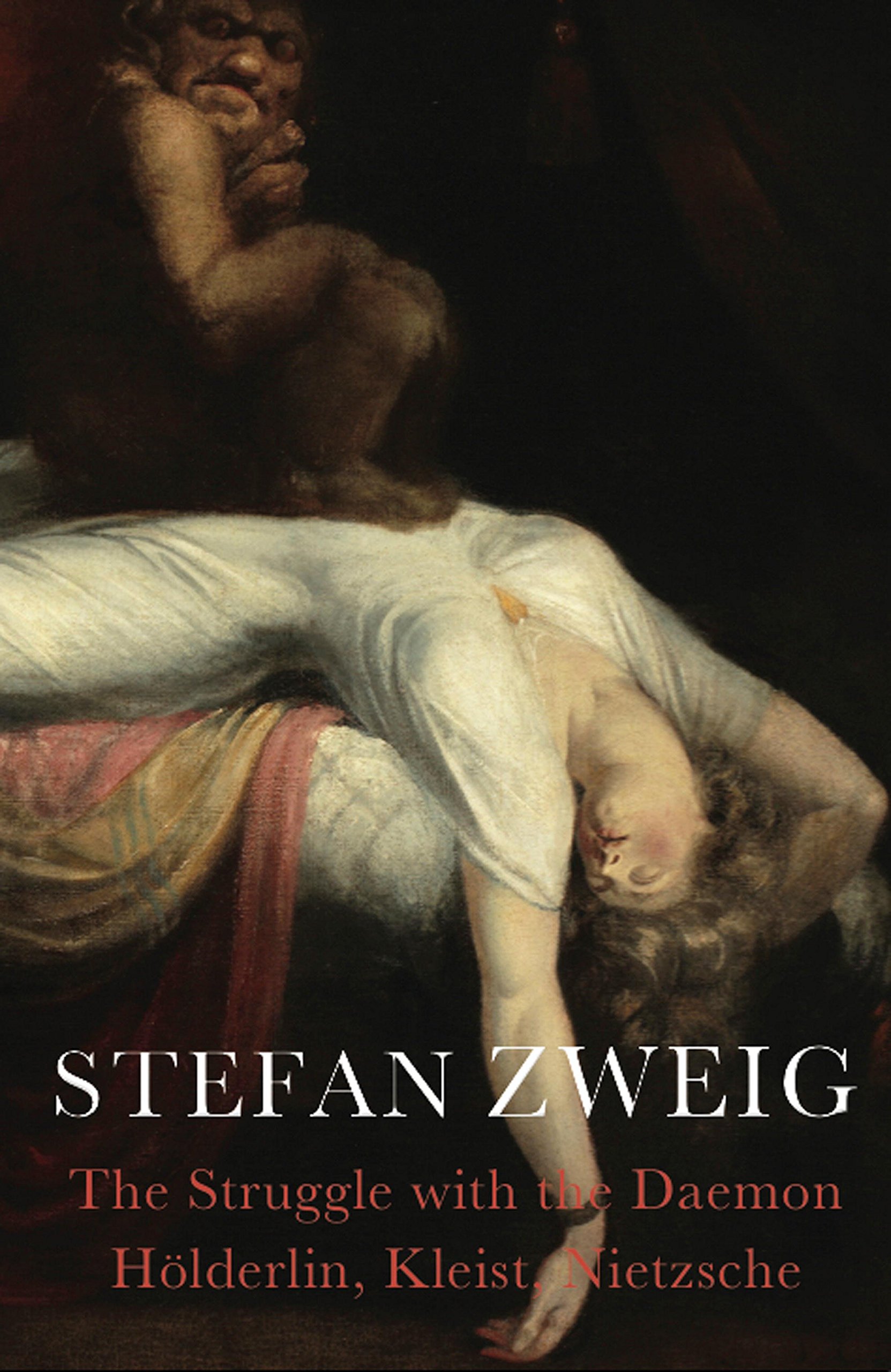
STEFAN ZWEIG
The Struggle with the Daemon Holderlin Kleist Nietzsche
引言
“一个凡人越难解放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迈耶
我不想探寻任何思想家的公式,只想刻画思想的形式。
公式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贫乏,对比就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丰富。
如流星般闪耀着短短的光芒迅疾地冲进了他们的使命的暗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义,因为他们只是从无限驶向无限。
“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是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质之中。
这个魔鬼只有通过毫不留情地破坏有限之物、世俗之物,也就是它所寄居的躯体,才能回到它的故乡、他的本原之乡,即回到无限之中:它发端于扩充,却趋向于破裂。
每个精神的人,有创造性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与他的魔鬼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永远是一场英雄的斗争、一场爱的斗争,也是人类最壮美的斗争。
三个人都没有妻子儿女,就像他们的手足兄弟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一样。
在他身上,人间生活的重力不断增长,正如在那三个人身上精神的飞翔力不断增长一样。
这是一种美丽的生活之贫瘠,又是一种不幸的贫瘠之美丽。
歌德的生活公式是一个圆:闭合的线,生存的尽善尽美,永远回归到自身,从确定不移的中心到无限总是相同的距离,从中心向外全面地扩展。因此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巅峰,他的创造也没有任何定点...相反,魔鬼性的人表现形式是一条抛物线:快速、强劲地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升,骤然地转变,急剧地跌落。他们的至高点已濒临跌落点:就是这样,后者神秘地与前者汇合在一起。
“病态”这个词只适用于不具备创造性的低等世界,因为一种创造了不朽的病态已不再是病态,而是过分健康、极度健康的一种表现形式。
创造性也永远都是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一切意义之上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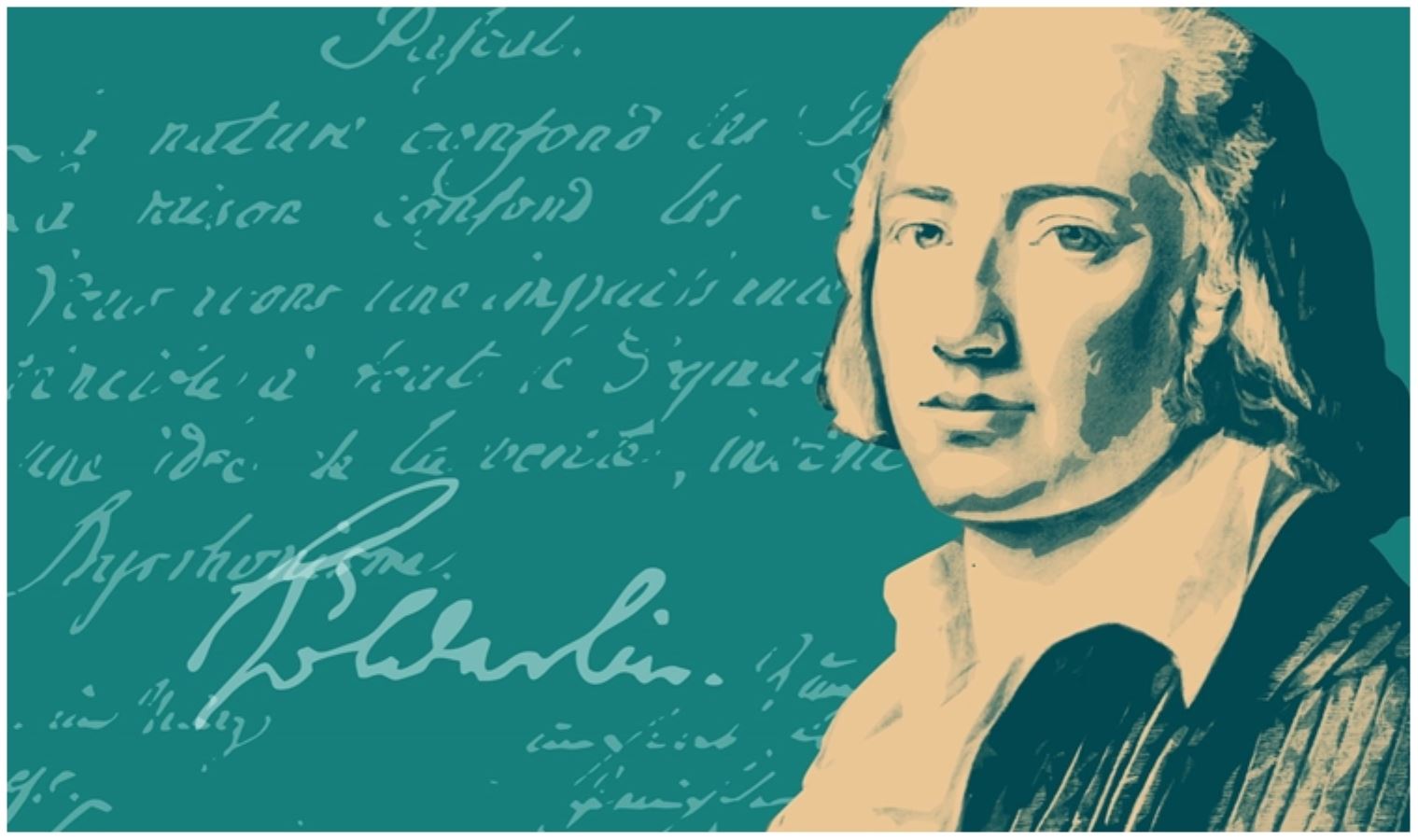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海子最喜欢的诗人
它用大镰刀无情地割掉自己的春天的幼苗。
像黑暗小屋中滴着泪的蜡烛一样过早地熄灭了...
当他有一天轻轻地躺下死去,这沉寂的消忘在德语世界击起的声音轻微得就像一枚秋天的树叶飘飘摇摇第落在了地上。
...这个神圣群体中最后的、最纯洁的诗人所留下的英雄的信息无人阅读、无人问津。
荷尔德林一生都是个没能学会生活的人...还与室友黑格尔和谢林一起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学。
像水银排斥水和火一样,他自身的元素拒绝任何化合与融合。
我不懂人类的语言,我在神的怀抱中长大。
他并不高傲,但却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种不易觉察的距离...
从一开始这个爱幻想的人就坚决地把生命的罗盘转向了永恒的方向,转向了那个永远无法到达的海岸,在这里,他的生命将跌得粉碎。
我的职业就是赞美崇高,为此上帝教我语言,还让我的心充满感激。
(余生中拨出时间来阅读你)
他就这样走上了那个看不见的祭坛,既是祭司,同时又是祭品。
“决定我的天性和我眼下处境的并不是固执。这是天性、是命运,也是唯一不能用恭顺来取代的力量。”
他相信的是天职,而不是成功。这个永远容易受伤的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披着龙甲的齐格弗里德---所有厄运的长矛都必将在其身上折断的人...
“少点儿也行,有点儿就行,没有也行。”
精神上最高贵的勇气永远是那种不带残酷性的英雄主义:不是毫无意义的反抗,而是面对强大、神圣的必然性义无反顾地献身。
人类从未教我这些,是一颗神圣的心无限深情地将我推向永恒。
就像苍穹以缤纷的色彩来填充天与地之间的空间,是为了无形中平衡星空与地面之间那种素有的可怖空虚,文学创作填补了精神的崇高与低下之间、神与人之间的鸿沟。
永生的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如果没有被有限制的生命所认识,没有被尘世所热爱,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被人的目光尽情饱览,玫瑰才真正成为玫瑰;只有在人类的视网膜中得到反射,晚霞才显得壮观美丽。正如人类为了不至堕落而需要神性一样,神为了获得真实同样也需要人类。
若信徒们不用心灵将他歌唱,他就无法在人群中找到真实的自己。
(很辛苦为的是几天忙碌后的休息。)
“向天才人物致意吧,他将砸碎你生活中的所有枷锁。”(砸碎很多枷锁,是不是也会套上新的枷锁的那些就不是天才?)
为尘世之人引来天火。
(牧师之孙荷尔德林和牧师之子尼采,都是弗里德里希...)
他的天赋比重很小,但却具有无尽的升力:荷尔德林的天赋与其说是艺术上的天赋,不如说是纯洁性的奇迹。他的天赋是激情,是看不见的翅膀。
“哦天雨!哦激情!你将人类的春天挽回。”
走进世界,如珍贵的种子,这些凡人的心在死壳中酣睡,直到他们的季节到来。
“那些对于别人只如轻擦一下皮肉的事情,却会使我血流不止。”(一提敏感就敏感)
只有在写诗时,他才是个大人;当他思考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孩子。
学生必须战胜老师来保住自己。
将会把他摧毁的东西,首先使他坚强;而使他坚强的东西,终将摧毁他。
“世界对我太残酷了。”
她像对待一个没有耐性的孩子一样温柔地照管着这个本该区照管她的孩子的人。
诗句像上涌的血从他咬紧的牙缝间迸发出来。
如果没有古老沉默的岩石---命运
的迎击,心灵的巨浪不会边做精神,
不会激荡得如此美丽。
“谁脚踏痛苦,谁就可以登得更高。”
(教人成功的那些,和农村相亲节录里小年轻的,直言自己就会挣钱和省钱...)
寒冷的黑夜里只留下风暴的咆哮
(当看美食节目也会有看电影的情绪,这疫情应该是就快结束了。)(只有一人是男儿)
(赶在时间击溃她之前,我想以勇士的豪迈冲锋,是时间的长毛同样也伤害了我。我和我的敌人一同倒下。)
纯洁的源头是一个谜,即使歌唱也难将它揭示。因为你怎样开始,就将永远怎样。
(同事日本留学的女儿在韩国进修语言,看了很多演唱会,新冠三天就好了。)
荷尔德林没有把生活转化为诗,而是从生活中逃进了诗里,像逃进了更高、更真实的生存现实中。
“我太怕生活中平庸和凡俗的东西了。”(总被在语言上攻击...大利发出水手的嘲笑声,而我竟有了信天翁的遭遇。)
诗比思想更有力,诗的语言比生活语言更自然...
“精神只能在热情中呈现,节奏只能服从于那种能让精神鲜活起来的东西。谁若想在神的意义上学习诗的创作,他就必须承认最高精神的无规则性,必须牺牲规则:不是随我所愿,而是随你所欲。”
荷尔德林第一次努力摆脱创作过程中的理智和理性而任自己被原始力量突袭。自从他排斥了规则,投身于节奏,那魔鬼式的激情就壮丽和谐地爆发出来。
(对这个民族的惩罚?)
残酷的现实要报复轻视它的人,那个他从不渴望去了解的世界也拒绝去了解他。他渴望爱的时候,只能收获到不理解。
(写完《北方50年》就看这本书,其实当时是犹豫的,如果先看过再写,估计会被影响到很大。写后再看,是很好的呼应,也是二次的自我认识。)
信心的桅杆和理智的舵盘已经完全断裂。
“神的箴言如雨落下,而那声音响自内心深处的仙境。”
(少儿部的存在形式是一种错误。)(应试变成畜生还是善于应试的畜生?)
如果说他狂热的天资是属于一个神性人物的话,那么他忧郁狂野的魔鬼也同样如此。
荷尔德林的迷醉却是纯洁的,因此他的离去并不是没落,而是向着永恒的英雄性回归。
火花在燃烧中消耗自身以忏悔,我们无能约束它。
我只是一片朝霞,漫无目的,倏然即逝。当我孤独地盛开时,世界还在沉睡。
克莱斯特---将自己的痛苦树筑死亡纪念碑
死了的橡树立在风暴里,而繁茂的却被雷电击倒了,因为雷电可以抓住它的树冠。
我对于你恰似一个谜。
但别难过,神对于我亦如此。
(四十岁喜欢阿兰·德波顿,五十岁要多读茨威格。)
而当它们,那些残暴的命运的猎狗,以为就要抓住他时,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壮美地纵身一跃,在成为低俗之物的战利品之前以一个高贵的姿态跌入了深渊。
对别人来说就像青春期的轻微擦伤一样可以快速愈合的东西,却像不可治愈的溃疡一样深深啮噬着他的灵魂。
他在一栏长的祈祷练习文中训诫姑娘要有美德,而于此同时,却连心灵中的神经末梢都认为自己是不洁的、有污秽的。
他必须穿过永远追猎的命运的灌木丛继续奔逃,直到逃至深渊为止。
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能力给自己制订一个生活计划,他就是而且永远是未成年的,他只能作为一个孩子生活在父母的监护中,或作为一个男人生活在命运的监护中。
他将那只他多年来幸福第陶醉其中的酒杯咣当一声摔碎在命运的墙上。
“耕一块地,种一棵树,养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一只狗...)
他投入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就像投入了深渊。
就像赫拉克拉斯从血淋淋的皮肤上撕下那件涅索斯衬衫一样。
地狱给了我半份天才,而天堂要么给人全部天才,要么干脆不给。而克莱斯勒,这个无度之人,只知道,要么全部,要么一点儿都没有,要么不朽,要么毁灭。
(英莹燕艳)
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价值而欢喜,那你必须赋予世界以价值。
人类力量所能做到的极限,我已经做了---甚至连不可能的都尝试了。我孤注一掷。那决定一切的骰子停下来了,它停下来了。我必须明白---我失败了。
(那些嗓子好的人唱的又是什么呢?那些长得好的人想的又是什么呢?)
“但愿上天赐给我的死亡有我的死亡的一半快乐和无法言传的幸福就好了:这是我能给你的最真心最诚挚的祝愿。”
比起活来,他更懂得如何去死。
“一个好的死亡往往是最好的生平。”
克莱斯特将自己的痛苦生动地竖成了死亡这座不朽的纪念碑;一旦得到塑造的恩泽,所有的痛苦就都有了意义。它成了生活的最高魔力。因为只有完全碎裂的人才了解对完美的渴望,只有被追逐的人才能到达永恒。(茨威格的死和他的这些了解或是发现有关吧。)

(读了尼采的部分,我也试着撕扯身上的那件衬衫,即便出现了血渍...)
尼采---以带血的痕迹划出时代精神
我对一个哲学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出榜样。(对一个老师的评价是他自己的学习情况。)(为什么要对公众说话,有时是要听到回声。)
...只是他以燃烧的翅膀飞跃的道路两旁空洞的里程碑,是冷冷的背景,无语的水彩。
这种“与自己同在”、这种“面对自己一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活悲剧的最深层意义和唯一神圣的苦难...
不是从世界中,而是在血淋淋的撕裂中这个命运狂人像赫拉克勒斯撕下涅索斯衬衫一样从自己的皮肤上撕下那种燃烧的热情,只为能够赤裸着站在最终真理面前,站在自己面前。(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斯普特尼克)(伍尔索普)
“毫不留情地做认识自我的人,做自己的刽子手吧!”
英雄的风景中没有天空,宏大的演出没有观众,沉默,越来越强大的沉默包围着精神孤独的可怕呐喊---这就是尼采的悲剧。
锤子越是有力地凿在他身上,他意志的坚硬石块就越发出愉快的声音。在痛苦这块烧得通红的铁砧上,随着每一次双重的敲打,那用以给他的精神包上一层坚硬的盔甲的公式被锻造得越来越结实,这是“人类之伟大的公式,对命运的爱:即人类不想要别样,不想向前,不想后退,不想躲如任何永恒之中。对必然的东西不仅仅是承受,更不是隐瞒,而是热爱。”
(手机未必是新的,树还是原来的树,但人是新的人,软件是新的算法,有新的分辨率,所以重复的路也是新的路...)
被我唤作命运的我心灵的天意啊,你在我之中!在我之上!请保护我,留给我一个伟大的命运吧!
对风度的激情不属于伟大,甚至谁若需要风度,那他就是虚伪的......要小心所有风度优雅的人!
他内在的树干宽广地隆起,有能力承受最狂暴的重压,他的根深深地扎进那个德意志健康的牧师家族的土壤中。
作为有机体的体质,尼采精神的肉体基础是的确很健康的。只是神经太脆弱......
巨大的痛苦面对的是强大的痛苦承受能力,太剧烈的感情面对的是动力系统遍布着的太细腻的神经。
在别人身上毫无反应的最细小的变化在他身上都会用颤抖的痛苦发出信号。
与懂得聪明地绕开危险的歌德相反,尼采总是极度鲁莽地行事,用身体直向危险冲去,抓住公牛的角...将这个纯粹敏感的人深深地逐入痛苦,逐到绝望的深渊边上:但正式这种心理学,正式这种精神性又把他重新拉回健康之中。像他的患病一样,尼采的康复也来自于一种天才的自我认知。
(长期服务的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人更不是人本...)
那种纯粹遗传的、毫不动摇的熊一样的健康是迟钝、无知地自足的。
我更加了解生命,因为我常常先险些失去它。
(这个社会继续变糟吧,人类留下的食量足够我去吸收了...)
这种疾病之后的第二次健康,这种不是盲目地获得,而是迫切地渴望过,粗暴地强迫过,用千百次叹息、呐喊和危难换来的,这种“征服来的、忍受来的”健康比起一直健康的人那种麻木的舒服要几千倍地有活力。
在他身上唱赞歌、凯旋的不是生命,而已经是死亡,不再是认识的精神,而是抓获了牺牲品的魔鬼。
对于尼采,这个悲剧人物,这个英勇的人,在这场同认识进行的伟大游戏中,重要的不是“对于生存的可怜追求”,不是更高的安全,不是一道抗拒经历的防护墙,而只是不要安全,只是用不满意,用不知足!“一个人怎么能够身处存在那绝对奇妙的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中而不去探寻,不因对探寻的欲望和兴趣而战栗呢?”
重要的是永远具有活力,而不是永远活着。
不隶属任何一种宗教,不效忠任何一个国家,翻倒的桅杆上飘着不道德的黑旗,前面是他疯狂地觉得与之手足情深的神圣的未知、永远的不确定,他就这样不断地为新的危险航程做着准备。
“...我抓住的一切都成为光,我放开的一切都变作炭,我定然是火焰...”
尼采式的正直与商人们那种家畜一般被驯化的、完全受节制的谨慎天性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与有些思想家那种两眼都戴着眼罩,像公牛一样只朝一种真理、只朝他自己的真理猛冲的敦实鲁莽的正直也同样绝少联系。
在认识之事上,“盲目不是错误,而是胆怯”,好心就是一种犯罪,因为谁若对羞耻和疼痛有所顾虑,对剥开时的喊叫、赤裸时的丑陋怀有恐惧,谁就永远不会发现最后的秘密。
(对人的善总报有幻想,对人的恶总是估计不足,所以受伤连连...)(即便语言上偶有胜记,可一身粪便和一脸狗屎有什么分别呢。)
“不会蜕皮的蛇会死掉。思想精英们也一样:如果人们阻止他们去变更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不再是思想精英。”
是他们那个圈好的道德篱栅的纵火者之前,他们就已经把他视为敌人了。
“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总是束缚于一个人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已经发现了自己,那他必须试图不断丧失自己---然后再重新找回。”他的本质就是持续的转变,通过丧失自我来认识自我,也就是永远地变化,永远不成为一个僵化、稳定的存在,因此“成为你所是的人”就成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存在的唯一一条生活命令。
“我的书谈的只是我的超越。”“我们是精神世界的漂泊者。”
他对北方、对德国、对故乡的心意已定的拒绝不是来自思想,不是来自理智,而是来自神经、心灵、感觉和内脏。
当他像一只蜥蜴一样享受着阳光,心灵直到最后的神经末梢都被照亮时...
在南方,在这所“理智和感性都恢复健康的伟大学校”里...
(余生的每次一快乐都要珍惜,而对每次一苦恼都要直面?)(为什么要依附一段并不纯洁的感情来表明自己的纯洁呢?清泉出自泥土?岩石...)(教人成功和农村相亲节目里那些自称只会挣钱活省钱的小年轻的又有多少不同...)
“哦孤独,你是我的故乡。”
在七千万人口的德国却只能找到七个他可以赠书的人...
(更衣室里像是甲板,大利发出水手的嘲笑,我体会到了信天翁的无辜...)
如果你长时间地盯着深渊里看,深渊也会盯进你的心。
尼采的崩溃是一种光明致死,是精神被自己的突闪的火舌烤成了焦炭。
谁被这样的飓风吹过心灵,谁就会听不见任何人类的话语了。谁被魔鬼这样深地盯住眼睛看过,谁就永远瞎了。
伟大就是:指出方向。
(天冷了,多喝了一碗鸡汤。虽然少有暖心的话...)
“没有英雄主义的时代,只有英雄主义的人。”将它确立于世界中并且永远只为自己确立的总是单个的人。因为每个自由的思想精英都是一个亚历山大,他在狂风暴雨中征服了所有行省和帝国,但他却没有继承者:一个自由王国总是会落在追随者和统治者、评论者和解释者手中,奴隶又回变成谈论对象。
自由意志是尼采最终的意义---他的生命的意义和他的毁灭的意义:就像大自然在否定自身存在的斗争中为了能够释放自己的强大力量而需要旋风暴雨一样,每个时代的精神也都需要一个魔鬼般的人用他强大的力量来反抗思想的共同体和道德的单调性。
这些富有英雄精神的叛逆者与那些安静的创造者是同样伟大的教育者和塑造者。
On this day..
- 世间最美的情郎 - 2010
- 熟练记忆当是应试第一良方 - 2008
- 鲁哥救我 - 2007
- [读书]人的毕生发展 -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