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Move: A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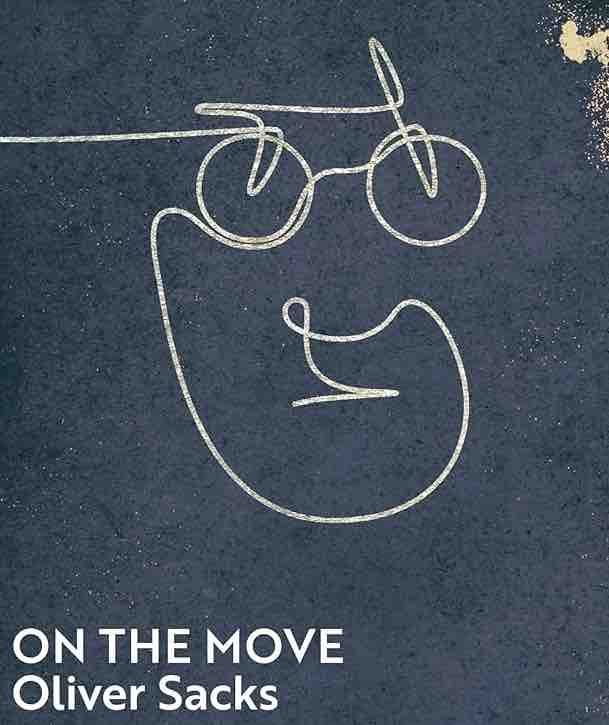
每条弯路都通向自我 奥利弗·萨克斯
以自己为病例,用一生去探索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治愈之旅
要想生活好,必须向前看;但要理解生活,只有向后看。-克尔凯敦尔
(估计是冲着书名下单的。传记读起来轻松,笔记能记录的不多。)
辗转
萨克斯会走得很远,如果他没有走过头的话。
在牛津大学,通过大一期末考试的学生才算正式入学,我此前已经获得了公开奖学金。我没能通过第一次预考,第二次,第三次,院长把我拉到一边,“这个傻不拉几的考试却老是考不出来?”我第四次参加考试,总算通过了。
我们试戴一种特制的眼睛,观察颠倒过来的世界,没有什么体验比看到颠倒世界更奇怪的了。然而几天后,大脑就会适应并调整视觉世界(只有在受试对象摘下眼镜后才会再次颠倒世界)。(gay这个形容词本意为快乐的)
离巢
小丘引出小山,小山融入群山,海拔越来越高,地势越来越崎岖。
她觉得精神分裂症已经夺走了她的一个儿子,唯恐同性恋又会夺走另一个儿子。
他有时称我们其他人,非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腐朽的正常人”
27岁生日那天离开英国,为了原理我那悲惨的、无望的、没有得到适当医治的哥哥。另一个种意义上,也驱动我在病人身上以我自己的方式探索精神分裂症以及相关的大脑思维障碍。
旧金山
从小就对搭档关系很着迷,读过基尔霍夫和本生的故事,饶有兴致地阅读了沃森和克里克的论文
肌肉海滩
遥不可及
为了获得十分之一克的纯镭而加工成吨的沥青铀矿。
我在药物带来的兴奋中对未来的神经病学工作和写作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愿景,我的目标极其明确。直到今天,我还在践行它。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周见圣戈尔德医生两次。
我经常眼睛一花,把出版publish看成惩罚punish
戴维起先给予法拉第各种鼓励,然后试图阻断他的事业。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爱丁顿和钱德拉塞卡身上,都是因为后生开始超越长者。
不能说我能与法拉第或钱德拉塞卡比肩,弗里德曼不是戴维或爱丁顿,但我认为同样致命的动力在起作用,只不过我们所在的层面更卑微。
觉醒
我越是了解每一个学生,就越觉得他们都与众不同。我给的全A并非制造平等假象,而是对每个学生的独特性的认可。我觉得,作为医生,不应当把个体简化为一个数字或一项检查结果。同理,也不应该把个体学生弱化成一个分数或者一张试卷。
我觉得写作帮我理清了思路。
我前所未有地感到心如明镜,对人生头等大事了然于胸,悟到了生与死的寓意。
你必须超越临床,你的文字要有寓意,要有神秘性,要表达你的内心需求。
究竟果壳那么小,还是无限大。(即便被困在果壳里,也是无限空间的君主。)
山上的公牛
他们七窍生烟,一路怒视着我们。
“让你最后的情意都是谢意。”
我在普通的社交场合很害羞,无法轻松地聊天。
事关身份
我在澳大利亚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想用分号替代文中的一个逗号,问我是否同意。要不是他的推动和鼓励,有很多文章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写。
“世界上一定有过两位造物主。”
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了解该发展过程的独特性尤为重要,因为他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孩子。原创性的关键是将缺陷减分项转化为补偿加分项。
如果一个孩子在这一关键时期没有习得任何语言,那么以后的语言学习就会变得非常苦难。
失聪父母生育的失聪孩子长大后会“说”手语,但健听父母养育失聪孩子往往长大后什么语言都没有掌握,除非很早就接触手语社区。
锡蒂岛
同情心的匮乏限制了你的观察力。
人的同情心往往到了三十多岁才会发育。
旅程
心智新观
(师生、父母与子女,大都在冲突中成长。这是所谓的极性。但成长似乎不满足渐变,某个时刻突然顿悟呢。)
“感谢上帝,我活到了今天,听到了这个理论。”
牛的大脑选择了特定的神经元群,强化了它们的活动,逐渐造就了这头奶牛。
(我放大了我教育的意义,尽管我特别留意一些细节,但其实呢,孩子随便走别的路径也都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许更好呢。但上帝让我们走在一起。)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神经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一生注定独一无二,我们都在自我发展,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家
我在度过了七十五岁生日后不久遇到我钟情的人,比利是位作家。
那段时间我多愁善感:我喜欢音乐,日暮时分迟迟不去的金色阳光,都会让我流泪。
我的一生必须做出深刻的、堪比地质变化的改变;我在一生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我那种内隐的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都必须改变。
我从14岁开始写日记,据最近一次统计,我已经写完近千本笔记本。
我的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我自己也不常看,但它们是一种特殊的、不可缺少的自言自语。
我需要通过写作来思考,而写作不一定非得用笔记本不可。
不管怎样,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这本书里只提到了少数。请其他人放心,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将来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和情感中,直到我告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