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
Lewis Thomsas 刘易斯·托马斯作品 (高密)李绍明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译者序
1987年冬天在美国的朋友建议下读了这本小书...
在一片四化、改革、振兴、崛起、腾飞的鼓噪中,在城市繁荣、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景象中,也存在傲慢与麻木、自私和短视、难以忍受的拥挤和污染、对大自然的不负责任的破坏以及人口问题的困境(那个时候的人口问题困境和现在不同吧)。
他指出进化论过分重视种的独特性、过分重视生存竞争等缺陷,而强调物种间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认为任何生物都是由复杂程度不同的较低级生物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论为我们指示了理解物种多样性的新途径。
(生态以生物细胞、化学分子组成的组织不同于物理原子或电子等细节的角度看问题,也有一种生活哲学的味道。)
细胞生命的礼赞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生命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世界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屏蔽着死亡。
我有一说,可以满有理由地讲,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像过去一向设想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
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呢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额遗传信息。
我有一说。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
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单个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我有一说。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看做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
如果它不像一个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东西呢?我忽然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地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可以用作倒计时的一些想法
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有生之物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关系,是程度不同的共生关系;看似敌对时,它们通常保持距离,其中的一方发出信号和警告,打旗语要对方离开。一种生物要使另一种生物染病,那需要长时间的亲近、长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办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会为我们接纳它假如球籍而孤苦地等待。我们这儿没有独居生物。
(年龄越来越大,越觉得自己进步,或许说明人人生的艺术性,而一个人的科学能力前25岁就定了。)
作为生物的社会
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
虽然我们比蜜蜂更相互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觉到我们的联合智慧。
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片片断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事件。
这种技术,这种使得许许多多以微薄的贡献进入人类知识库的技术,乃是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秘密所在,因为它获得了一种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发出的共同的、集体的力量。
有一件事让人叫绝:探索(explore)一词不能适用于探索活动的搜索一面,但却起源于我们在探索时发出的声音(拉丁语explorare有喊出之意)。我们愿意认为,科学上的探索是一种孤独的、静思的事。是的,在最初一些阶段是这样。但后来,或迟或早,在工作行将完成时,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彼此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章,给编辑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
对于外激素的恐惧
在宿舍里贴近居住的年轻女子,她们的月经很容易自动同期进行...
每一次回大陆并邂逅女孩子时,他的胡子都长得快得多。
这个世界的音乐
从数学上来看,不可避免地要使物质组织成越来越有序的状态。由此产生的平衡行为是带化学键的原子不停地组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子,同时出现贮存和释放能量的循环。
从热力学上讲,它势必要把物质重新安排成对称形式,使之违反几率,反抗熵的增加。
一个诚恳的建议
我提一个诚恳的建议。我提议,大家先别采取进一步行动,等我们获得关于至少一种生物的真正完全的信息再作道理。那时,我们将至少能够宣称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医疗技术
说味
这种动物能嗅出同卵双生子的相同气味,并且交叉地跟踪两人的踪迹,好像那些踪迹是一个人的。
很多善于思索的人都作出过关于球形动物的想象,而开普勒则曾认为,地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物。
鲸鱼座
一个长期的习惯
托马斯·布朗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愿意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也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像苍蝇一样死亡。
大多数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着死亡的准备。那一过程对旁观者造成的痛苦大大超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
死亡毕竟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它所形成的机制同样注意入微,有利于保护生物特性的遗传信息指引着生物通过死亡的每一步,像我们司空见惯的生命的所有其他关键活动一样。
曼哈顿的安泰
群居性最强的动物只能适应群体行为。蜜蜂和蚂蚁离群只有,除了死亡别无选择。实在没有单个个体这种生物,它并不比从你皮肤表面放逐出来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生命。
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倒更像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
昆虫的行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机制严格定型和决定的;它们很少甚至全然没有学习的领悟力和能力,它们缺乏一种根据许多世代累积的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当然,这类东西只自己一个人读还是一宗不完全的安慰。要获得充分的效果,需要好些人一齐朗读,需要许多口唇同步活动。
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你环顾四周,寻找一些我们集体地和无意识地从事的事业,寻找一些我们像造马蜂窝一样建造出来的东西,而我们个人却不知自己在干什么。
只有在很小的事业中,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励。
自治
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教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
没有我的干预,它们都会更幸运。
想一想,你得操心怎么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朵听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功夫干别的了。
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电波,指挥细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合,不接管,而是学着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
作为生物的细胞器
(开放的世界,不是让我觉得自己的渺小,而是放眼看整个人类的渺小,特别是民族的渺小。和之前的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伟大的自信相比,我看到了我立足的低洼之处,而盐碱地也是有生物的,只是一定是没什么参天的大树了...)
说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为我自己的肌肉呼吸着,却是一帮陌生客。
*细菌
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细查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像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扯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不满了地雷。
(活在当下,遗憾最小框架,贝索斯)
我们的健康
社会谈
一个蜂巢就是一个球形动物。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一志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来做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己的永久性。
我们不像土蜂那样,被基因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
实际上,从长远看,我们大概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为社会性的好。
有一件事越来越令人不安:似乎语言的天赋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我们大家标记为人,把我们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
信息
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赋。
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像鸟有羽毛一样。
任何意义不清,任何游移不定,都会给这些细胞带来严重的危险,而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危险则更大。
临近的细胞就会被视为异己而卷进反应。有一种理论说,衰老的过程可能就是由这种误差的累积造成的,是信息质量的逐渐降低。
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像我们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锁定的信息,还能驰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法识别意义中多钟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暴尸野外
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前早早死去。若不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砂砾。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是可恨的事。
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
自然科学***
科学研究的开端是由彻头彻尾的惊讶组成的一片乱糟糟的领域。
工作着的科学家就像按遗传指令行事的动物,似乎是根植于人体中的本能在驱动着他们。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尊严,但还是像动物幼崽一样在作着胡闹的游戏。每当他们接近一个答案,他们都毛发倒立,汗流浃背,沉浸在自己的肾上腺素之中。抓住答案,抢先抓住答案,就是他们最强的驱力。跟这一驱力相比,什么取食、育儿、保护自己不受自然力的侵害等等,都不再话下了。
一个热门学科就像一个巨大的智慧蚁穴,单个头脑几乎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头脑群体中,每个头脑都各自携带着信息攘来挤去,以光的速度交相传递着信息。
零零碎碎的信息飞扬四散,扯成碎片,崩溃瓦解,被鲸吞蚕食,突然,峰回路转,悠然一曲,关于自然界的一条新的真理出现了。
需要的只是创造出合适的气候。要叫一个蜜蜂酿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阳导航和合成碳水化合物的法规。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为单个的蜜蜂活不成),然后尽可能把蜂房周围的总体环境安排好。像蜜蜂酿蜜一样,气候适宜了,科学到时候自然就会出来了。
(人的培养,也就是教育,就像科学的出现,也像是蜂蜜的出现,人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是环境,而不是对人的再造...)
自然的人
我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种表述方法就死,地球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球状生物,其所有的有生命的部分以共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照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纵者,至多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换一种专司信息接受的能动组织---或许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那个最好的世界里,我们的作用是整个生物体的神经系统。
或许,我们是被侵略者,是被征服、被利用的一方。
我们最应该忧心的环境无疑是我们自己。
伊克人**
伊克人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人种...
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
这是本让人泄气的书,果真像他所暗示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只是伊克人。
如果把我们孤零零地撇在一旁,我们将变成同样的无欢乐、无热情、互不接触的孤独动物。
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吃不开、兜不转的社会中,你也会建立自己的防御的,伊克人就是这样行事。每一个伊克人成了一个团体,是人自为战的单人部落,是一个选区。
城市具有伊克人的全部特征,在人家门口阶上排便,在自己和别人的河湖里排便,到处倾倒垃圾。它们甚至设立机构来遗弃老人...
国家在本性上是孤独的,自我中心,离群索居,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没有感情这东西的。
...我们还没学会在聚群而居时如何保持人性。
@qiusir:刘易斯·托马斯的《伊克人》真是一篇神作。伊克人(Iks)的小小部落从前是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人种...这些人似乎生活在在一起,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孤独的伊克人,在被毁的文化废墟中被孤立起来。他们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防御...每一个伊克人成了一个团体,是人自为战的单人部落...城市具有伊克人的全部特征...国家是最像伊克人的机构了...
计算机
我们有一天会开始为我们自身软件开辟禁猎区和保护区,以免我们像鲸鱼一样消失。
我们的最神秘之处在于我们的集体行为。除非我们理解了这种神秘,不然就造不出像我们一样的机器。
...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输出的信息比收集的还要多。信息是我们的能源,我们为它所驱动。
我们进行大量的集体思维,大概比任何社会性物种都要多。
我们不像昆虫那样因进行集体思维而备受赞美,但我们仍是这样干着。
我们都着迷于尽快地往机器里输入信息,但缺乏多多收回的感觉机制。
科学的规划
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两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
生物神话种种
语汇种种
不同的词融合,然后交配,杂交词和作为野生变种的符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
关于几率和可能性
我们的本性是违反概率的。
而在我们生存的数十亿年中成功地继续了这一努力,没有漂回到那随机状态,这简直是数学上的不可能。(现在物理学在小数点后一百位的精确度努力,另一方面,未来的物理是不是在大宇宙行为的规律上出现类似爱因斯坦对牛顿的颠覆呢)
每一个都在描述着生的机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细胞的表面都载有特殊的蛋白质构型的标记,每个人都可由指尖那块皮上的指纹,甚至还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气味辨认出来。
我们有种平凡感,也是我们的惊异减轻。
人的大脑是大地上最公开的器官。它向一切开放、向一切发出讯息。当然,它掩藏在头骨之中,秘密地进行着内部的事物。
我们在大脑之间传递着思想,如此具有强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类的众多大脑在功能上常常显得是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关于自我的整个可爱的概念---认为自我具有自由意志、自由进取心,是自主的、独立的孤岛这种古老的奇思妙想,原来是一个神话。
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间还机器短暂,不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
...对于人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是额叶有了新皮层。
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
世界最大的膜
大气本是无情物,很难跟它动感情。然而,它却又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产物,就像葡萄酒和面包。
我们应该称颂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的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
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的地球表面早就会像月球表现一样....但我们还是知道有它而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像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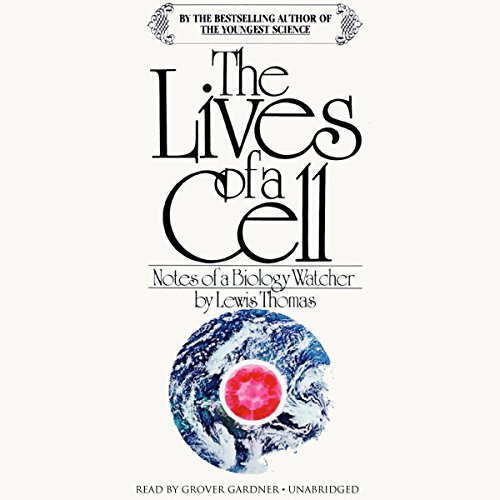
·年末温习20221202
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
地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有生之物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关系,是程度不同的共生关系;看似敌对时,它们通常保持距离...
有一件事让人叫绝:探索(explore)一词不能适用于探索活动的搜索一面,但却起源于我们在探索时发出的声音(拉丁语explorare有喊出之意)。(某种程度上尤里卡...)
说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正确的语法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像鸟有羽毛一样。
科学研究的开端是由彻头彻尾的惊讶组成的一片乱糟糟的领域。
我们输出的信息比收集的还要多。信息是我们的能源,我们为它所驱动。
On this day..
- 求师得图标折纸 - 2024
- 求师得的巴比龙 - 2024
- 缘分到了,题自然就会了 - 2018
- 力的作用点的位移 - 2012
- 长得像我们的几位... - 2007
- 学生上网? - 2006
- 学习的脸皮厚与不要脸 - 2005
- 上帝是人!人是上帝? - 2004